“身體作為建筑”肢體雕塑工作坊是深圳市當代藝術與城市規劃館“知覺城市——新文化設施的創意與構筑”展覽的延展和補充。展覽在梳理深圳歷年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浪潮,展示深圳未來幾年規劃建設的公共文化設施項目的同時,試圖提出一個方法——以“行走”作為媒介,將身體和知覺投入真實的城市現場。建筑不是冰冷的現實,它應賦予大眾多元的空間親歷和生活體驗,成為公眾探索城市的對象、公共事件發生的載體。同時,公眾和事件的介入也將重新定義城市場所,塑造公共生活方式和精神氛圍,讓城市滋長出共享的公共精神。

一座城市的歸屬感源于日常生活中難忘的地點、具身性的親歷體驗和感知記憶所織補的個人敘事網絡。這種與城市的深度情感鏈接,基于一種“行動主義”的介入,調動身體將物質空間在某個時刻轉化為獨特的活動場所,形成個體專屬的城市印記。
“行走”在20世紀中上葉已成為了備受關注的社會實踐議題。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拱廊研究計劃》中的文化形象“都市漫游者(flaneur)”作為資本主義高速發展和消費主義盛行下的自主消解,打破以效率為行走目標的現狀,通過隨機、偶然的“閑逛”讓城市的豐富性得以展現;20世紀60年代,盧修斯·布爾克哈特(Lucius Burckhardt)的“漫步學研究(strollology)”產出了感知環境“序列(sequences)”的概念——社會高速發展和交通工具的廣泛普及讓個體在兩個地點之間的行進過程成為“點狀”而非“序列”,人們感知世界的身體經驗存在缺失。克哈特在巴塞爾大學的漫步學課程中組織了多場行走實驗活動,為風景園林師和城市規劃者提供了新的視角——在真實空間中行走以發現城市問題,進而分析、塑造我們真正需要的城市環境;2013年起,以本雅明“都市漫游者”為靈感創刊的德國社區街道主題雜志“Flaneur”,開始每期挑選一座大城市中的街道,進行為期兩個月的采風和駐地和編撰。雜志團隊采用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漫步觀察策略,扮演街頭的“記者”“偵探”“藝術家”和“作家”,以當地居民的第一視角去捕獲由這條街道的影像、繪畫、文字構成的復雜敘事,揭開街道的面紗。這些自下而上的“行走行動”成為了某種文化觀察的方式,以及個體對城市現代性的反饋。
深圳市當代藝術與城市規劃館圍繞“知覺城市“展覽策劃的“身體作為建筑”肢體雕塑工作坊也是這樣一次社會實驗行動。活動由劉赫、李可淳、柯志宏、黑晨爽策劃,在走讀導師劉赫和肢體導師徐奕欣的帶領下,10位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生活背景的參與者運用“行走”,以深圳福田市中心區為“田野”,觀察、記錄承載歷史和記憶的具體地點,并觸發自我與城市的情感連接。在步行于福田中心區地上、地下街道后,挑選一處對于自身具有獨特意義的地點進行肢體創作。



那么,當我們真正地步行在城市街道,會發生什么?
也許會被路邊植被的香氣吸引,發現街道地面的紋理,遇見迎面而來的人。在行進的過程中,我們以身體為尺度去丈量周遭,接觸并融入人群,讓身體充分參與到城市空間的各個節點當中。通過這個過程串聯身體經驗和思維認知,突破視覺中心主義的慣性,把對城市的認識由視覺擴充至嗅覺、聽覺、觸覺、味覺等一系列交織的綜合體驗。

我們采取的隨機行動無不引導著新的城市事件發生,我們允許任何事物闖入思維,用承載著經驗和記憶的身體來建立與城市的連接。在角色趨向同質化的社會現實中,我們將想法和體驗外化為城市的一部分,生產出獨特的個體敘事,確立自我在城市中的“位置”。“行走”成為了抵抗并補充現代城市生活的時間加速和空間拓張的方式,將城市中的個人和集體認知經驗進行重新梳理、整合。

面對城市現代性的內在張力,我們“行走”于不斷流變的實體空間,通過建立起與外部世界的內在關聯,打開個體的全面知覺,收獲個體的穩定感和獲得感。同時,也讓城市滋長出共享的精神特質。
也許,認識一座城市,就是從一場不需理由、不限時長、不設目的的行走開始。

免責聲明:市場有風險,選擇需謹慎!此文僅供參考,不作買賣依據。
關鍵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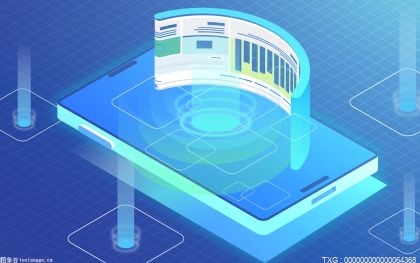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